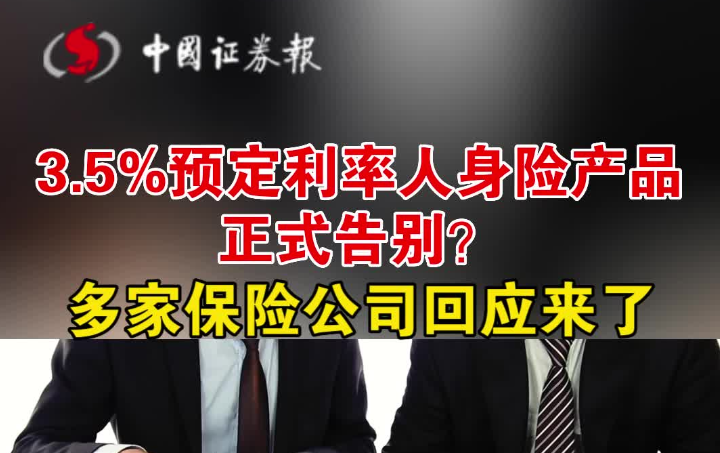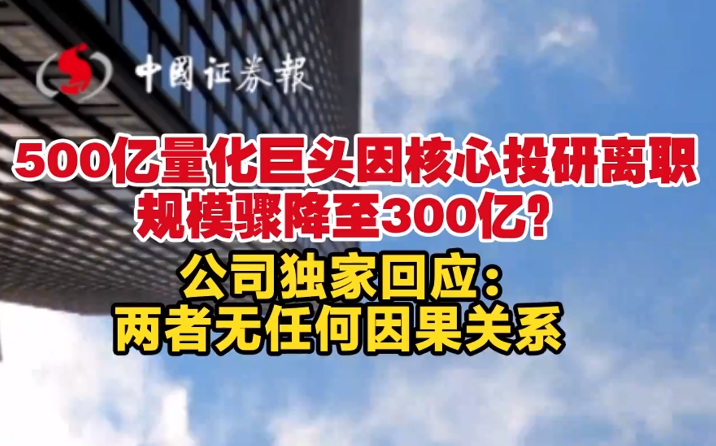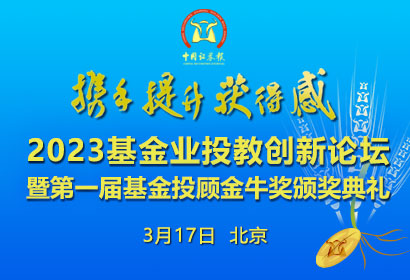新一轮区域工业化转移带动大宗商品周期上行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副院长 解学成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院研究员 聂天奇
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宗商品价格经历长达十几年的下行周期,直至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大宗商品价格触底回升,CRB现货综合指数从2020年初的400点附近一路飙升至2022年5月的阶段性高点644.07点,至今仍然在560点附近,累计涨幅约40%。至此引发市场对新一轮大宗商品周期的关注,并对未来周期走势产生一定分歧。
2008年以来CRB现货综合指数走势

数据来源/Wind 视觉中国图片 制图/杨红
目前大多数研究认为,大宗商品价格与经济周期、金融周期都具有高度相关性,且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笔者侧重于从区域工业化视角分析大宗商品价格周期,并以此研判未来的周期趋势。
1900年以来,全球主要经历四次大宗商品长周期,分别对应历史上几次大规模区域工业化建设。当前,逆全球化下的“近岸化、优岸化”产业链重构,正在通过新一轮区域工业化转移带动大宗商品周期上行。从当前共建“一带一路”的进度来看,未来区域工业化建设需求仍然具有较大潜力,尤其是我国西部地区、印度和越南。同时,逆全球化下的全球关键矿产竞争还将长期影响部分大宗商品供给,从供需两端对大宗商品价格产生影响。
大宗商品经历四次超级周期
自1900年至2022年的122年时间里,基本每30年大宗商品价格就会出现一个阶段性高点,大宗商品价格经历四次长期波动,并在波动中出现一定分化。较为显著的是能源、贵金属及金属矿产价格涨幅,以1900年为原点计算,累计涨幅分别为355.98%、142.23%、22.28%。食品价格在农业实现现代化生产后逐渐走低,谷物价格累计增长为-57.42%,肉类价格仅增长5.01%。此外,自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取而代之的“石油-美元体系”显著提高了大宗商品的波动幅度,尤其是能源及贵金属价格。
商品价格由供需决定,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周期的本质逻辑是:新经济增长点引发的需求冲击与供给端产能提升的相对滞后导致价格波动。对大宗商品超级周期进行滤波处理(剔除长期趋势及短期波动)后发现,一个完整的大宗商品周期长度普遍在30年左右,而一轮价格上涨的持续时间往往在15至16年,此后在供给达到峰值后价格进入持续下降区间。是什么因素导致长达15年左右的需求上升?
笔者认为,任何单一产业崛起引起的原材料需求往往是短期的,而大宗商品价格在长周期中的持续上升显然需要规模巨大且持续的需求提升。比如,区域范围内的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即某一国家或地区在由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时,需要投入大规模城镇化建设。这一过程将带动从住宅、基建、厂房所需的钢铁、水泥,到家具、家电、纺织品所需的石化类、金属类需求持续提升。例如,美国的城镇化建设、二战后重建、亚洲四小龙及中国的工业化崛起,均符合上述拉动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需求,也与历史上四次超级大宗商品周期吻合。
从全球矿产的供给端来看,产能达峰的时间也基本支持上述逻辑,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金属矿从勘探发现到投产所需时间平均约16年。在下游需求迅速增长,上游原材料产能缓慢爬升时,将引起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上升。此外,地缘政治冲突因素也将从供需两端推高大宗商品价格。两次世界大战前夕也均处于前两次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起点,之后全球范围内的热战转向以局部代理战争,以经济、军事对抗的冷战以及以金融狙击为主要手段的货币战为主要形势,也分别推高大宗商品价格。因此,将重要历史事件及大宗商品价格变化趋势相结合,可以发现,国际政治集团对抗、局部热战、工业化转移几乎是每一轮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开启的重要因素。
新一轮大规模工业化转移正在发生
在每一轮超级周期回落到底部后,往往伴随另一个区域工业化的出现引领下一轮超级周期,为什么区域工业化转移会在全球范围内接替发生?
理解这一问题需要抛开经济的短期波动,从世界主要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历史中寻找答案。根据库兹涅茨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倒U曲线来看,伴随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居民收入差距不断上升,大量生产向大量消费过渡时,会达到贫富差距的峰值。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先进国家的工业化及城镇化会使资本在原始积累下趋于充裕、产能逐步过剩、劳动力价格上涨、企业利润率下降。此时,过剩资本需要向低成本国家转移,过剩产能也需要通过出口消化。在资本和产能寻找低成本国家的过程中,低成本跟随国将逐步进入工业化,逐步消化先进国家的过剩产能,同时其生产的低价商品有助于降低先进国家的物价水平,提升先进国家居民的实际购买力。
从十九世纪末英国的产能饱和出现开始,制造业开始向欧洲大陆和美国转移,承接产业转移的美国开启工业化进程,并通过两次世界大战的“韬光养晦”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此后伴随美国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开始将部分制造业转移至亚洲国家,带动了亚洲四小龙及中国经济崛起。过去国家间工业化转移的周期规律显示,随着地区工业化进程加速,在经济高速增长中产生的过剩产能需要对外转移,以拓展市场,降低生产成本。
过去中美两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也较好阐释了上述理论。中国加入WTO后进入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时期,通过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在美国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没有大幅增长的情况下,提高了其中低收入居民的实际购买力。同时,大量贸易顺差形成的美元又通过投资美债的方式回流美国,支撑了过去美国经济的长期低利率、低增长、低通胀“三低”现象。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由加工出口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型,部分过剩产能也面临对外转移需求。而美国的深度消费型经济正逐步面临产业“空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美国需要“制造业回流”以重新支持美国经济。在两个经济大国同时面临产业结构转型之际,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大规模工业化转移也正在发生。
共建“一带一路”按下“加速键”
从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来看,未来最具备大规模工业化和城镇化基础建设的地区应处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洲地区,该地区的工业化及基础设施建设进程或将按下“加速键”。
2021年以来,美国持续推动制造业回流,但目前来看,美国本土制造业的回流效果并不显著。2022年以来,美国ADP制造业就业人数占非农就业人数比重延续下滑态势,2023年5月相比2022年初下降0.2个百分点,主要还是因为美国高昂的经营成本。相较于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回流,美国对其他国家产成品的进口额大幅提升,主要包括墨西哥及亚洲地区。
从出口结构来看,伴随我国人口增长拐点到来,低劳动力成本时代成为历史,人才红利将逐步替代人口红利,同时,“双碳”目标的约束也使高污染企业面临产业转移。自2018年开始,部分中国企业逐步向周边更低劳动成本的地区转移,极大促进了周边地区的区域工业化。
同时,共建“一带一路”有望拉动沿线国家及中国西部地区的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一带一路”沿线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近65个,总人口约44亿,劳动力充足,且工业化发展空间巨大。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口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均值低于50%,其中南亚国家仅为44.7%,中东欧国家为47.7%,远低于54.2%的世界平均水平,人口红利显著。此外,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巨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含中国)的铁路总里程约32万公里,平均密度为8米/平方公里,低于中国的12米/平方公里,远低于日本和美国的62米/平方公里、23米/平方公里。人均年用电量不足1700千瓦时,低于3125千瓦时的全球平均水平。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17年至2030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或将高达26万亿美元,平均每年为2.5万亿美元。
共建“一带一路”的推动与实施,直接涉及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且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及建筑业。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庞大基建及基础工业建设需求,近年来我国已与沿线国家签订一系列投资项目合同。根据商务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202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数据,2021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中,制造业占比为39%。2022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承包工程额达1162.60亿美元,占我国对外承包工程总额的51.2%。
此外,过去我国外向型经济建设以东部沿海地区的海上贸易渠道为主,近年来沿海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已相对完善,而共建“一带一路”及西部陆上交通要道的打通,将继续拉动过去投资欠缺的西部地区基建投资,打开中国对外贸易的“西大门”。
国际资源竞争扰动大宗商品供给
以上地区的工业化及基础设施建设,在未来较长时间内将持续拉动大宗商品需求。同时,逆全球化趋势下,各国对关键矿产的限制性政策还将影响部分大宗商品供给格局。
国际政治集团对抗是大宗商品周期的重要影响因素。美苏冷战期间,双方囤积大量储备矿产,导致大宗商品价格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持续上涨。当前,各国针对关键矿产、战略性资源制定了一系列政策。
自2020年以来,以智利、秘鲁、阿根廷、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资源大国不断出台政策限制矿产出口、外资参与及境外冶炼,推进矿产资源的国有化,这使矿产资源的逆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全球关键矿产的竞争正在解构过去的“矿产资源全球化”格局,推高全球资源的加工生产成本,可能导致部分关键资源供给受阻,且不排除伴随竞争进一步加剧而导致战略性超量储备需求。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大宗商品长期价格趋势与区域工业化密切相关,且由于政治及经济发展规律,区域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接替发生。当前,新一轮区域工业化转移或将在亚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引领大宗商品需求持续上升。同时,逆全球化下的关键资源竞争也可能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供给受阻,需求端及供给端同时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将推动新一轮大宗商品长期周期持续上行。